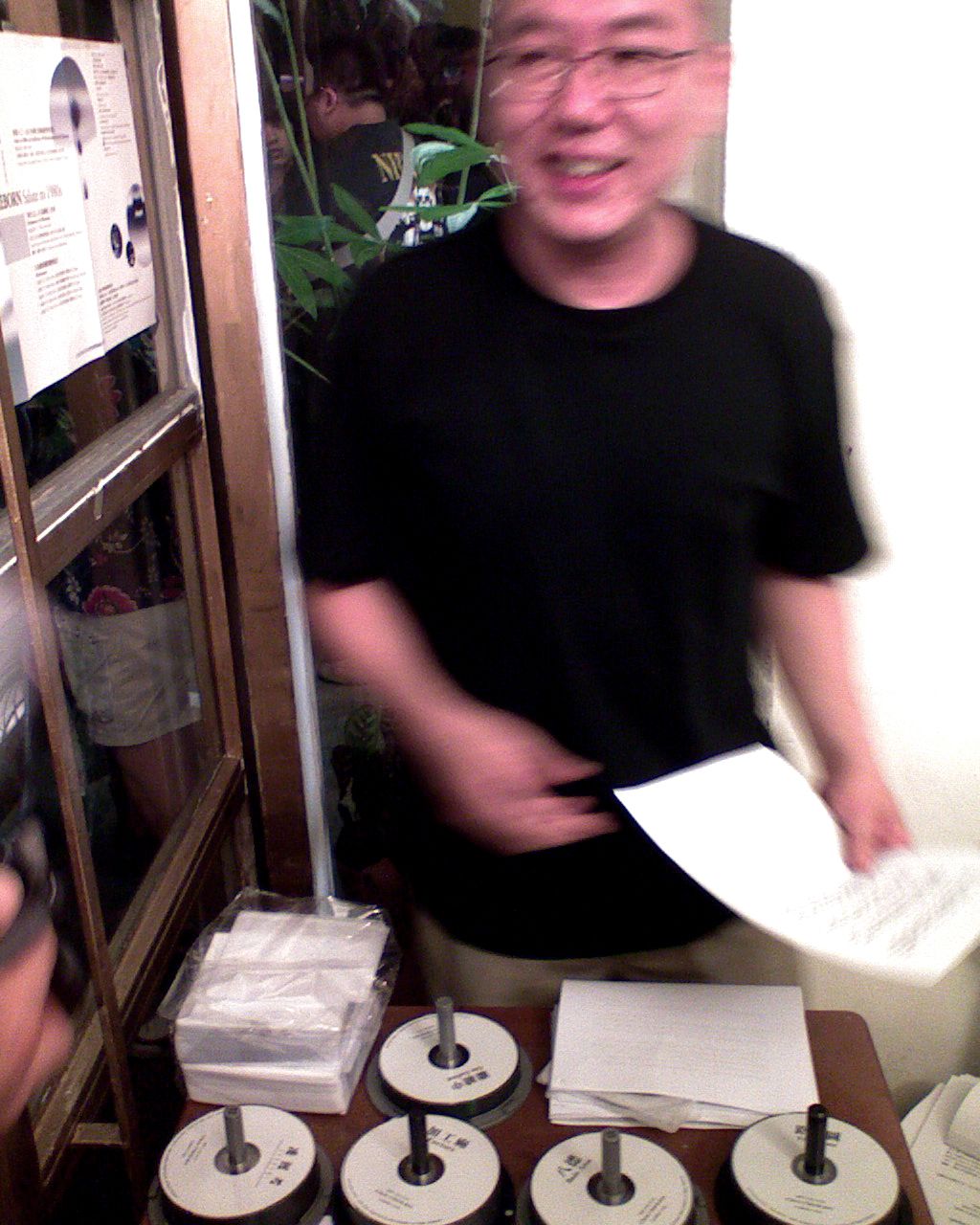
(圖為陳界仁《自我盜版》,在牯嶺街小劇場入口處販賣自己的錄像作品,一片50元整。)
李銘盛是本文開場,也是這個藝術節的開場。一個絕妙的開場。他搶了主辦單位本來要做的事,而且做得異常賣力。
他跑去機場接機。
香港藝術家魂游一入境,就被李銘盛的歡迎布條給嚇到了。那是一個大得離譜的布條,入境大廳內不知情的群眾很納悶,以為是哪位名人訪台,但大多數人確實連「魂游」是不是個人名都不太確定。
包括魂游在內,這次「台北國際行為藝術節」一共邀了13位外籍藝術家參展,加上15位台灣藝術家,陣容十分浩大,所有行為表演得拆成三天發表,單場票價200元,三場合購特價500元,即便人最少的第一天,要擠上觀眾席仍有點困難。沒買票的人有別的選擇,新竹東門城及台北師大公園有兩場免費的「國際觀摩演出」,活動開幕前兩天,「行為藝術工作坊」及「致敬八○:GLT台灣行為藝術資料展」已率先起跑。
以行為藝術節之名
這是2007年「行為藝術在台灣」的場景:近1/2外籍藝術家、近1/4女性藝術家、室內售票演出外加戶外觀摩表演、工作坊、史料展與講座,一個不折不扣的國際藝術節。雖然論人氣,這個行為藝術節仍像是個藝術圈裡的小眾活動,但若以台灣行為藝術的發展脈絡作考察,此等規模已非20幾年前的藝術家所能想像。李銘盛的接機排場放在這裡,竟也不算太過分,那塊大布條就像是對整件事的隱喻──關於它的盛大,它的代表性,它的國際交流意味。
事實上,1980代作為先驅的他們也來了,除了李銘盛、陳界仁之外還有林鉅。他們不只是資料展中的史料,更是現場表演者。整個藝術節,穿插著不同年紀的藝術家身體,最年長的莫昭如(香港)生於1947年,最年輕的藝術家是丁禹仲(台灣)生於1982年,那年,謝德慶正在紐約戶外與生存搏鬥,進行他第三個作品計畫,而台灣在地的行為藝術場景也正萌芽,李銘盛與陳界仁,都在隔年創作了他們第一件行為作品。
從一種身體盲動,變成藝術類型,再成為一個藝術節,20、30年的在地脈絡已化為可以致敬耙梳的對象。但這個體制化的進程,並無法簡化為一條單線的,從「行為」到「行為藝術」再到「行為藝術節」的語意擴充,相反的,它是接枝後的再生。如今被「致敬」的那些藝術家,並非在1990年代推動行為藝術展演體制化的人。近五年在台灣漸成氣候的「行為藝術節」,其實一直是從小劇場裡延伸出來的支脈,最早是王墨林組「身體氣象館」在1992年開始策劃國際性的身體表演活動,以行為藝術之名還是後來的事。相較於1990年代以來,許多視覺藝術出身的藝術家之身體實踐,大多是現場沒有觀眾、僅靠錄像與文字紀錄的個人行動,這條「行為藝術節」的脈絡更具有一種現場表演的劇場模式。這次活動對於1980年代的「致敬」,大有整合兩條歷史脈絡的企圖。
究竟台灣1980年代的行為藝術場景是否可概括為一種時代性?可能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這次活動確實存在著某種跨越國界的、以「純粹的身體」或「抵抗的身體」作為核心價值的感覺。在此之中,力道與疲憊同樣重要。如黎利亞‧雪爾德(Lilia Scheerder)把自己綁在一張吊床上掙扎,柯德峰把自己限定在15分鐘的時間內哭泣,王楚禹把自己限定在物理性之中,妄想推動腳下的島嶼。最經典的作品無疑是霜田誠二的《桌上》,他把自己定在一張桌子上,裸身從桌上翻到桌下再翻上來,當這具中年男人的裸體氣喘噓噓、顫抖地在桌面上緩慢動作時,沒有人會否認它有多像一具台座上的雕塑。事實上,霜田誠二這件在1990年創作的作品,已巡迴世界各地展演過無數次,1992年曾來台發表過。
但就在觀眾屏氣凝神之際,莫昭如一上場卻用諧擬的方式,幾乎是惡狠狠地揶揄了一遍。莫昭如的調戲,提醒了我們有一些藝術家確實在採取不同的創作路線。包括莫昭如在內,魂游、吳方州、林世偉等人都透過了荒謬、詼諧的手法,來諷刺歷史、政治、社會與集體記憶之類的議題。如果這種輕盈與架空,仍太仰賴符號意義與行動意圖,在葉怡利與紅毛(鄭詩雋)那裡,這些東西則透過綜藝化的手法而幾近被放空。葉怡利《KUSO──彩虹七仙子》以令人目不暇給的服裝道具,重覆無意義行為(十分近於「天線寶寶」的神韻);紅毛則是以歡愉之姿行使暴力,在鼓樂之後砸爛鐵箱,釋放困在箱裡的蝴蝶。對我來說,他們的作品距離那個純粹或抵抗的身體已十分遙遠。
此外,這次活動也有不少藝術家在行為之中加入媒體技術。其中最令人激賞的是帕斯卡勒‧葛侯(Pascale Grau)的《室內》,她先以自己的腹部當舞台,拉起衣服揭開序幕,依序加入各式小物件,上演有如玩具屋般的劇碼,透過攝影機即時捕捉並隨後重播,再於現場加入人聲效果。巧妙地運用身體及媒體的界面轉換,造就一種現場的奇幻效果。但近年來由水墨擴展到錄像的吳少英,在現場用各式飲料製作液體動畫,卻僅僅像是一種「工作室開放」的創作示範,放在整個藝術節之中反而有些失焦。
丟向觀衆的羊屍
同樣使用錄像,林鉅紀錄了他如何把一頭羊屍從海邊扛回家裡,如何洗淨、去皮。但他的現場行動遠較這個紀錄影像來得令人震驚。
他把這頭羊屍帶進場,當著觀眾的眼前宰卸,並敵意地望著觀眾。這場剖屍暴力被他操演成一場安靜的祭典,已先行處理過的羊屍幾乎是不帶血的。安插好的演員則在一旁扮演獵奇的觀光客,身為觀眾席的我們開始自我投射,「你就是那名觀光客」,但一種劇場的觀看倫理卻仍讓這種投射停留於象徵層次──直到林鉅向觀眾丟出屍塊,前排觀眾驚呼走避為止。
或許應該這麼說,藝術家充滿敵意的眼神,望向的其實是瀰漫場中的一種「看表演」的默契,這與藝術節的架構自然脫不了關係(我們可是付費進場的不是?)。對如今越來越世故、越來越懂得在表演後鼓掌的藝術觀眾來說,行為藝術對他們最大的冒犯常常是無聊,而非驚嚇。就當表演結束,工作人員進場抹地,包含前排走避的觀眾在內,現場響起掌聲。「幹嘛鼓掌?」坐在我旁邊的觀眾丟下一句。
我猜想,這句冷場話應該才是林鉅要的。這不只證明「前衛藝術的冒犯」仍是可行的,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飛向觀眾席的屍塊動搖了原本以為有一條隱形的線隔開場中與場外的劇場框架,讓身在觀眾席的我們,不只是必須有所回應,還得思索這個回應,不管是鼓掌或是憤怒。觀者轉變為批判性的觀者,一如法斯賓達(R.W. Fassbinder)「反劇場」的理想。
被毀棄掉的傳統劇場觀看倫理,造就了一些藝術家夢寐以求的現場感。但顯然並不是所有台上或台下的互動,都足以拆解掉「看表演」的默契,相反的,某些友善的互動極可能是另一種默契下的產物。特別是在這種劇場化的行為藝術表演中,邀請觀者上台或藝術家走向觀眾席「一起互動」,似乎已成了廣被藝術家採納的手段。但或許是劇場情境所致,大多數上台的觀者儘管不知道接下來將發生什麼,仍存在著勉力配合演出的動機。
有時候,這種互動很類似成長團體的心理治療氣氛,如葉子啟《手語》裡一連串由藝術家發動、觀者跟隨的行為程序即是例子。在另一些作品中,觀者則被預設為一項媒材、一個活道具。李湘軫的《狀況內》就包含了這樣一個道具般的觀眾,與所有物件同置於一個框線內,成為藝術家所有權的一部分。在葉怡利那裡,觀眾則是莫名其妙被捕獲的一群獵物。
丁禹仲是對此互動性需求最大的藝術家。待他湊足了觀眾人數,將大家用一條繩子圈在一起時,台上的人竟比台下的人多,表演者與觀者之間的權力關係產生微妙改變。我以為最妙的不是藝術家如何擠在人群裡,用他的鼻子嗅聞每位觀眾的體味,而是觀眾們甘於以這種方式被對待。直至有人無法忍受,自繩圈中逃脫時,已是表演尾聲了。
斯卡裘的兩個評論
觀察這種「看表演」或是「參與表演」的默契在每件作品中被毀棄的狀態,往往較之它們的應用來得有趣。甚至我覺得這是現場行為藝術最振奮人心的瞬間,它包含了藝術家與觀者之間某種精神角力。對此,最精采的一幕發生在澳門藝術家吳方州作品的後半場。那時他已將活雞矇上布套,綑上膠帶拖行了一段時間,雞早已嚇到腿軟,一些觀眾看不過去,衝進場中解放動物,觀眾開始鼓噪,拿起藝術家丟來的紙團當作武器丟回去,場面有點亂,一些觀眾開始笑了。「This IS performance!」藝術家亞倫‧斯卡裘(Alan Schacher)在台下喊著,聽來是個讚辭。
我注意到斯卡裘也是唯一拒絕丁禹仲邀請上台的人。就在他搖頭說不時,我開始意識到關於藝術家與觀者間的默契這回事。我認為斯卡裘這兩個「評論」,有助於我們釐清在這樣劇場化的「行為藝術表演」中,所謂「互動」及「現場」的意義究竟為何?當觀者參與表演,成為作品脈絡的一部分,很容易產生一種主體性的錯覺,但或許我們應該要在這些被設定好流程的互動情境之外尋找回應,從觀者的拒絕、憤怒或是一句冷場話為線索,由此,我們將能獲得一種批判性的角度,來理解這個由「看表演」與「參與表演」所架構起的行為藝術節體制。